归纳推理的合理性问题,你知道吗?
【刘建平】归纳合理性的哲学辩护及其思考
作为现代逻辑的主要分支之一,现代归纳逻辑远未取得象演绎逻辑那样受重视的辉煌地位,甚而至今都没有一种公认成熟的、统一的现代归纳逻辑体系。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始终无法回避其自身的根基性问题——归纳推理的合理性问题,即“归纳问题”。通常将该问题分解为二:归纳过程中,由前提过渡到结论的逻辑中介是什么?如果没有,应该怎样为归纳推理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这个问题最早由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提出,故又称“休谟问题”。
休谟关于归纳的责难对后世许多逻辑学家无疑是一大挑战,他们把为归纳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当作一项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说,休谟问题引起的“思想上的困难有时差不多成为感情上的痛苦”[1] 4。为保持归纳推理在逻辑学和方法论中的正当地位,后世逻辑学家提出了种种辩护方案。
一古典归纳论者的归纳式辩护
归纳式辩护企图在传统经验辩护的基础上作出新的努力,以克服休谟提出的经验辩护,势必引起循环论证的困难。该方式的提出者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逻辑学家穆勒(J. S. Mi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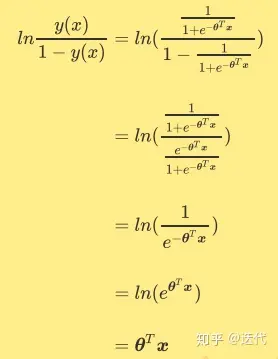
在坚持全归纳观点的基础上,穆勒把归纳定义为“发现和证明普遍命题的活动”[2] 185。他认为只有(不完全)归纳推理才是真正的推理,逻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此类归纳进行研究。在他看来,休谟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培根归纳逻辑的不完善。为此,他在培根三表法的基础上整理出一套探求因果关系的归纳方法——“穆勒五法”,并进而给出了该问题的归纳式辩护。“穆勒五法”的共同特点是,把那些没有与被研究现象a恒常一致地相联系的现象B、C、D等排除掉,而把唯一留下的那个情况A确定为被研究现象a的原因或结果。但A就一定是a的原因或结果,难道a不可以没有任何原因或结果吗?穆勒提出“普遍因果律”作为对策,即:任一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原因,并且同因产生同果。“普遍因果律”又从何而来呢?对此追问,穆勒不得不拿出作为其逻辑学最高原则和最终归宿的“自然齐一性”原理,认为“自然齐一性是归纳的基本原则和普遍公理。”[2] 201或者说,普遍因果律只不过是自然齐一性原理在具有先后关系的现象中最具普遍性的表现和一个特例。这样,就为归纳辩护的问题归纳为如何确立自然齐一性原理的问题。
如果说,休谟的怀疑论使归纳法和经验论逐渐沉寂,那么到穆勒则又重振了归纳逻辑的威风和对归纳可靠性的信心,仿佛休谟问题的阴影正一步步远去。然而这种威风和信心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没有任何依据能够确立这个原理。演绎推理不适合,因为如果前提中只包含关于过去和现在的知识,那么结论就不能够告诉我们未来的自然过程将是齐一的;归纳推理同样不适合,如果用它去确立自然齐一性原理,显然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于是,自然齐一性原理受到了和归纳推理同样的遭遇,一起被推到了理性的审判台前。对此,穆勒解释说:“如若考察自然的实际过程,我们便会发现这假定(自然齐一性)是有根据的。据我们所知,宇宙是这样构成的,在任何事物中保持为真的东西,那么在该类事物的所有事例中均保持为真。”[2] 201显然换位思考的哲学原理,这种辩解很无力,穆勒也因此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思量再三,他选择了以退为进,宣称自然齐一性原理并不为归纳推理提供逻辑辩护,而只是逻辑辩护的必要条件。这种方式的确避开了循环论证,但接下来他却在对归纳分层的前提下,运用以前曾大加驳斥的演绎三段论为工具企图作出进一步解释,这又导致了其自身体系的不一致。
显然,作为穆勒论证基础的自然齐一性原理是不充分的。他不仅没有科学阐明该原理的合理性,甚至连原理本身的具体含义也未能解释清楚。因此,穆勒的辩护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成功。后来的事实表明,倘若不放弃对归纳结论绝对确定性的寻求,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出路。即便如此,穆勒的辩护依然是有价值的。它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重建了归纳逻辑,丰富和完善了古典归纳逻辑的内容,穆勒被视为古典归纳逻辑的集大成者,当之无愧。
二现代归纳主义者的演绎式辩护
如果说归纳式辩护是从避免休谟提出的以归纳说明归纳的循环论证入手的,那么演绎式辩护则是以克服休谟提出的演绎逻辑不适于归纳辩护的困难为着眼点。其思想出发点是,归纳推理虽达不到演绎必然性,但其结论的真值却可加以逻辑或数学的测定。具体是指把数学中的“概率”概念引入逻辑中,用概率论的定量分析和公理化、形式化的方法探索有限的经验事实对一定范围的普遍原理的归纳支持和证实程度,为归纳提供逻辑或数学的基础和证明,从而扫除归纳疑难。此种思想倾向代表了现代归纳逻辑的发展趋势,代表人物有凯恩斯(J. M. )和卡尔纳普(R. )等人。
概率作为一个数学概念,其古典含义在于对给定条件下不同的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程度及其相互间关系的数量刻画。归纳逻辑引入“概率”,是想凭借数学方式把握归纳结论和归纳前提的关系,甚至给归纳逻辑也搞出一套形式化系统,从而使归纳逻辑彻底摆脱掉传统的心理习惯基础,朝着精确化方向发展。但由于各逻辑学家对概率的解释不同,现代归纳逻辑实际上是许多本质不同的系统同时并存,从而对归纳问题的解决也是形式多样,精彩纷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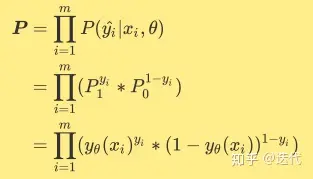
作为现代归纳逻辑的真正创立者,凯恩斯对概率的解释与古典概率论的主张就极为不同。他认为,概率是两个命题或命题集合之间的一种二元逻辑关系。令命题集合h为前提,命题集合a为结论,如果对h的知识使得我们能对a有程度为r的合理信念,那就称在a和h之间有一个程度为r的概率关系,记作a/h=r。这一定义通常被称作概率的逻辑关系解释。在凯恩斯看来,概率的大小取决于前提知识的范围,若前提涉及到的知识范围大小不定,则概率也大小不定。但这并不否定概率的客观性。因为一旦h确定,对a的合理信念度也便是唯一确定的。正如凯恩斯所说,“概率的理论之所以是逻辑的,因为它讨论的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合理信念的程度,而不是个人实际的信念。”[3] 4可见,凯恩斯那里,任何两个分别作为前提与结论的命题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并且只存在一种概率关系,既然a/h成立,并且h是已有的前提,那么对结论a有程度为r的信念就是合理的。合理信念度由命题间的概率关系决定,而不是相反。
至于概率的测度和比较,凯恩斯认为,归纳前提和结论间的概率取值范围是(0,1)。但并不是任一概率都可以用具体的数值来测度,从而也并非任意两个概率都能比较大小,甚至有些概率间就不具有可比性。概率可测度、可比较的必要条件是各种可能结论满足所谓的“对称性”,从而能够运用“不充足理由原则”的那些场合。但事实上,归纳推理的结论在一般情况下都不满足这些条件,故而归纳结论的概率值在很多时候都不能以具体数字来测度。这样一来,将归纳逻辑的重心放在计算此类概率值上便显得困难重重。不如换个角度从另外两方面考察:(1)相对于一定的前提,归纳结论是否具有不为0的概率?(2)如果是,能否通过一定的途径使之得到提高?在凯恩斯看来,如果此两个问题能得到肯定回答,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即可得到辩护,归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凯恩斯提出并严格证明了后世所谓的“证实基本定理”。该定理大致是说,在归纳结论相对于原有的知识(前提)具有不为0的概率的基础上,事例数目的变化总会引起事例之间正类似或负类似的增减,从而对归纳结论的概率产生影响。进一步,一切与已有事例不同的事例都能导致归纳结论概率的提高。这一定理显然为问题(2)提供了证明。此时问题(1)的回答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它既是上述“证实基本定理”的前提,又是归纳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的关键。为此,凯恩斯提出“有限独立变化”假设加以说明。该假设是说,世界上的一切性质归根结底都由数目有限的基本性质产生而来,任一对象可能具有的无限多种性质都从属于这些基本性质或由这些基本性质组成的“群”(指基本性质的合取)。由此归纳推理的合理性问题,你知道吗?,如果任意两种性质x、y恒常的为某些对象共同具有且尚无反例,则它们同属于一个群的概率或y属于x所生成的群的概率就是非零的有限概率。换言之,相对于一定的前提,归纳结论的概率并不为零。显然,这种建立在假设之上的解释既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归纳推理的合理性问题,你知道吗?,又陷入了和穆勒类似的困境。“有限独立变化”假设不但无助于解释归纳结论的概率何以不为零,甚至它自身的合理性也依然是个问题。尽管如此,凯恩斯在归纳逻辑发展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仍然不可低估。一些人在凯恩斯方案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提出了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卡尔纳普便是其后继者之一。
和凯恩斯一样,卡尔纳普也主张概率的逻辑解释,并且在利用概率论解决归纳问题的道路上,他较前者走得更远。他甚至断言归纳如演绎一样具有分析性,从而使其早期辩护方案显示了浓厚的逻辑分析味道。令C函项表示归纳前提对结论的证实度,公式C(h,e)=r。按照卡尔纳普的解释,C(h,e)仅仅表达了h和e两命题之间的某种逻辑关系,而对h和e各自的真假情况毫无断定换位思考的哲学原理,不论对h、e赋以何值,都不影响该式的真值。换言之,该公式是纯逻辑分析的,它的成立源于前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蕴涵关系。只不过演绎推理陈述的是“完全逻辑蕴涵关系”,而归纳推理陈述的是“部分逻辑蕴涵关系”。例如,以h表示假设“X是黑头发”,e表示“芝加哥有300万人口,其中200万是黑头发;X是芝加哥的一个居民。”可以逻辑地计算出C(h,e)=2/3,尽管h可错或已错,尽管e也可能错误地报道了观测结果,但上述算式却不会错。它意味着假说h在2/3的程度上被证据e所蕴涵,即h相对于e的认证度是2/3。
我们知道,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扩大知识内容的推理,而仅依靠知识封闭型的分析陈述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正如W. 施特格米勒所说,卡尔纳普遇到了一个二难推理:如果e是一个关于过去的观察报告,C(h,e)=r是一个分析陈述,h则是一个关于将来的论断;那么,或者C函项是分析的,那么它就不能提供一个未来的报告;或者事实上有这样的报告,那么由于e是说明过去,h是说明将来,因而C函项就不可能是任何分析性陈述。卡尔纳普无法解决这一困难,只好作出原则性让步,即不把它作为评价和选择普遍理论的一般原则,而是作为一种关于个别预言的决策理论和在危险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准则。至此,卡尔那普最终放弃了为归纳提供纯演绎辩护的企图,转而求助对于实践决策的先验直觉辩护。这就是卡尔纳普后期所谓合理决策的概率理论,他甚至还提出“全证据要求”和“效用估计量取最大规则”来为之辩护。也就是说,在应用归纳逻辑以期获得可靠结论时,“必须把全部可获得的证据作为决定认识程度的基础。”[4] 108同时,在对诸多的行动方案加以选择时,则以效用估计量最大为标准。显然,这些规则的现实操作性很成问题,而且还遭遇到“无限全称命题概率为零”以及重蹈归纳问题覆辙的尴尬。可见,卡尔那普仍未摆脱归纳问题的幽灵,他最终只得向不可知论靠拢并得出结论说,要使归纳逻辑对获得合理决策有用甚至必不可少的基本事实是,人类还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将来。
三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实用辩护方式
这种方式企图跳出纯逻辑的圈子,转而借助人们的日常经验和归纳的实际效用为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寻求一种逻辑外辩护,其肇始者是皮尔士,主要倡导者则是莱辛巴哈(H. )。和卡尔那普等人对概率的逻辑解释不同,他找到了概率的频率解释并以此为据建立了自己的归纳逻辑理论。
通常来讲,概率与频率是两个概念,某事件的概率和频率一般情况下并不总是重合的。而莱辛巴哈却将二者联系了起来,认为概率就是相对频率的极限,即在某事件的无穷序列中,出现某一特征的相对频率的极限就是该特征相对于该序列的概率。该定义听似合理,但却难逃责难。定义中所说的无穷序列只是理想状态,究竟如何确定作为初始概率值的极限频率呢?甚至相对频率的极限是否存在都是个问题。针对一系列责难,莱辛巴哈提出了自己的“认定策略”,借以应对极限存在和极限不存在两种情形:当极限存在时,即在事件A的序列的最初n项中,若观察到特征B出现的相对频率Fn(A,B)=m/n,那就认定,特征B相对于A序列的频率极限(即概率)就是m/n。显然,特征B相对于事件A的频率是一个动态值,它将随观察次数的增多而变化。但这种变化始终围绕着一确定值上下浮动,随着观察次数趋向于无穷,该频率无限趋近于其极限。按照此方法,理论上总可以找到被考察事件的概率。对于极限不存在,即所考察的频率序列是发散的这种情形,莱辛巴哈也并不否定。他的解释是,若频率极限不存在,那用任何方法都不能找到概率;若频率极限存在,那用这种方法就一定能找到概率。也就是说,认定策略是诸多方法中最有效、最为可取的。
正是在这种实用原则的指导下,莱辛巴哈将“认定”概念引入归纳推理的辩护过程。他认为,休谟导致经验论垮台的根源在于一个唯理论公设,即一切知识必可证明为真。在此公设的笼罩下,归纳推理当然不可能证明为有效。正确的做法是,把归纳推理视为由前提(相对频率)认定而非推出结论(极限频率)的过程,进而把归纳结论同样视为一种认定,即一种虽不知其真假,但作为真的来对待的陈述。这样,归纳问题就转化为较弱意义上的由前提出发证明归纳结论是一个最佳认定的问题。“而这一证据是可以找到的”[5] 187。那就是借助概率度对认定作出评价,概率度越大,认定越趋向于合理。虽然该过程中仍包含着归纳推理的运用,从而仍然存在休谟问题,但这不影响人们将此结论作为最好的认定来处理。
把这一思路运用于对归纳的辩护,莱辛巴哈作出了直觉和技术两个方面的分析。直觉上,尽管预测未来时没有任何逻辑学和认识论方面的理由选择归纳,但归纳却是人们行动的最佳工具。因为面对未来,凡是其它方法可以预测成功的,归纳也行;但如果未来是不可预测的,那归纳以外的其它方法也是无效的。换言之,作为归纳结论的认定并非要根据事实情况来作真假判断,而是要根据最可能的成功来作出行动的决断。因此,在采取行动去预测未来时,最有效的手段便是归纳。技术上,当极限存在时,运用归纳可以将被观察到的初始阶段相对频率的值设定为该序列相对频率的极限值,并随情况变化作出相应调整;而当极限不存在时,不仅归纳,归纳以外的其它方法也同样无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归纳推理被作为最有效因而也是最合理的预测工具。显然,归纳问题在莱辛巴哈那里经过了改装,他实质上将对归纳原理的辩护由逻辑标准改为了实用标准,由休谟的“逻辑上是否合理”改为了“实际中是否有用”,同时又把辩护的条件由充分性降为必要性。这也正是后世称之为实用主义辩护方式的理由。
四关于归纳问题的哲学思考
纵观上述,从归纳推理合理性的几种辩护方案,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归纳逻辑从古典向现代演进的大致脉络。这一脉络同时也折射出归纳逻辑理论逐步克服自身缺陷、日益发展完善的过程。面对休谟釜底抽薪式的诘难和归纳问题对自然科学及其经验论的致命打击,早期归纳论者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他们急于寻求对归纳推理的绝对辩护,力图捍卫归纳结论的正确无误性。表现在方法上,即致力满足于制定一些粗浅的归纳法规则,探求在某些假设之下运用这些规则以得到确定无误的结论。随着概率理论的建立以及对前人失败教训的反思,后世逻辑学家逐步意识到必须从观念和行动上转变对策。他们更为客观理性地分析归纳推理的本质及其核心问题并进而给出了更为合理的辩护方案。在方法上,即首先承认归纳推理的概然性特征,承认归纳结论的可错性,在此基础上运用概率演算的逻辑工具致力于探讨归纳结论相对于其前提的概率、影响此概率的因素以及提高归纳结论概然性的途径。事实表明,这种转变是符合归纳逻辑的发展规律的,因而是正确的。尽管各家各派对概率这一工具的具体解释并不相同,其处理归纳问题的具体方式,从而相应的解决方案也相去甚远,尽管努力背后的问题依然存在,但归纳逻辑理论的研究却取得了真正的进步和长足的发展。
当然,具体到归纳问题的解决还应看到,即使上述各种方案倡导者的具体出发点、各自的相关证据以及最终的归宿并不相同,但他们在深层的思想根源上却存在着一些共同缺陷,从而招致了共同失败的命运。
首先,对演绎逻辑原则和推理必然性的极度崇拜是根源之一。从休谟提出问题,直到各家各派解决问题,其根本的逻辑出发点和思想根源,无一不是把演绎逻辑原则视为一切思维方法的最终的并且是唯一的依据,认为只有那些被该原则证明为合理的思维方法和原理才是有效的或正确的。这一观点本质上是把逻辑的必然性等同于认识上的有效性,从而把演绎逻辑当作了唯一正确的逻辑。正如陈波教授所说的,“休谟疑难……里面隐藏着对推理必然性或逻辑必然性的崇拜”,而这是可以受到挑战的[6] 258。因此,为挽救归纳推理必须摆脱对演绎规则的崇拜,并对其进行恰当的逻辑定位。
其次,对归纳本体论依据和实践必然性的绝对割裂也是问题解决中的一大思想障碍。从考察休谟问题的哲学基础来看,早期归纳论者大都拒绝研究归纳的本体论依据,而是将问题局限于纯形式、纯逻辑的圈子里来解决。这样势必割裂归纳逻辑与客观世界及其科学实践的联系换位思考的哲学原理,使归纳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一种空洞干涩的逻辑技巧。这一点在卡尔那普那里体现得最为突出。但是,逻辑学终归是工具,只有与具体学科知识相结合才能体现其真正价值。因此,归纳推理的合理性也只有在现实的科研活动中才能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辩护。对此,陈波教授曾说,“尽管归纳结论不具有必然的真实性,但归纳却是人类获取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知识的最主要的(在我看来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归纳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实践的必然性。”[6] 259因此归纳问题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纯逻辑学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求真”的问题。更为重要的,它是一个科学哲学问题,是一个与科学基础、科学性质、科学发展过程以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等密切联系的问题。关于归纳辩护的思考是不能与具体的科学发展史和科学发展实践相分离的。
再次,对归纳逻辑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片面理解也使得问题一直存在。从考察休谟问题的认识论基础来看,他们把认识看作是机械积累经验材料的单纯量变过程,否认理性对感性材料的抽象和概括等方面的能动作用。因此,无论其具体方式和所依据的标准如何不同,归根结底都是局限在经验范围内的差异,始终都没有越过自己在认识论中划下的鸿沟。其实,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发展过程。从方法论角度讲,认识活动既包含对经验材料的积累扩充,也包含对这些材料的理性加工和能动改造。而前者正是运用归纳方法和归纳推理进行,后者则主要依据演绎推导完成。不论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还是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归纳和演绎都是相互渗透的。因此,只有克服了对休谟问题认识论及方法论基础的片面理解,才能真正认清归纳过程的实质和效用,也才能在归纳问题的解决中取得真正的进步。
【参考文献】
[1]金岳霖. 论道[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J. S. Mill. A of Logic[M]. : , Green and Co. , 1925.
[3]J. M. . A on [M]. and Co. , , , 1921.
[4]洪谦. 逻辑经验主义(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莱辛巴哈. 科学哲学的兴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陈波. 逻辑哲学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