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学一做)习近平总书记以突出的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以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等五个方面来概括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而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只有时时保持旺盛的创造活力和蓬勃的创新精神才能不断发展、赢得未来。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基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通变”思想。“通变”思想强调的是历史持续不断地演进变化,反对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历史观念。“通变”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上》: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也就是说,占问的意义是穷尽卦象的根本思想而预知未来,贯通事物的演变过程而作出判断,阴阳的变化莫测显示了天地万物的神秘本色。天地自然无不处于一种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变化是整个世界的总体原则和基本规律。《易·系辞上》云: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法象莫大乎天地传统文学的发展现状,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名莫大乎日月。……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周易》以诗意的笔触描写了天地自然的演化过程,无论空间的天地、时间的四时,还是活动在时空中的人类,都存在于永不休止的运动变化的状态中。“通变”也称“变通”“会通”。《易·系辞上》云:“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易·系辞下》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在运动变化中寻绎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周易》的基本原则。而通变的本质是“生”,只有贯穿始终的运动发展才能保持本质事物的生生不息。“通变”一词的出现就是在“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系辞上》)的语境中提出的,“生生之谓易”是“通变”理论的前提,日日更新,生生不息,生命只有在流动变化中才能延续才有生机。有学者认为“通变”是“通”与“变”的组合,两者是并列的。其实“通变”一词,“变”是核心,“通”是以“变”为前提的。《易·系辞下》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这个逻辑线索中传统文学的发展现状,“变”是根本、是发源;只有在“变”中才能实现历史的“通”,才能达到永恒的“久”。
与通变哲学相呼应的是中国文学理论的“日新”精神。“日新”是中国古典哲学对创新意识的特殊的语言表达。《周易·大畜·彖》:“刚健笃实辉光传统文学的发展现状,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礼记·大学》谓: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这是“日新”思想的体系性表述,从商汤《盘铭》到《尚书·康诰》再到《诗经·大雅·文王》(两学一做)习近平总书记以突出的创新性,“日新”意识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历史线条。“日新”是人格道德之新,是精神的时时更新;“新民”意味着对民众的整体塑造,是集体性格的显现;而“其命维新”则是周人坚持的政治路线,“日新”的精神贯穿于人格、思想和国家政治的各个方面。哲学的“日新”精神,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日新”一词频频出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成为文学创新思想的经典表述,例如:
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原道》)
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馀味日新。(《宗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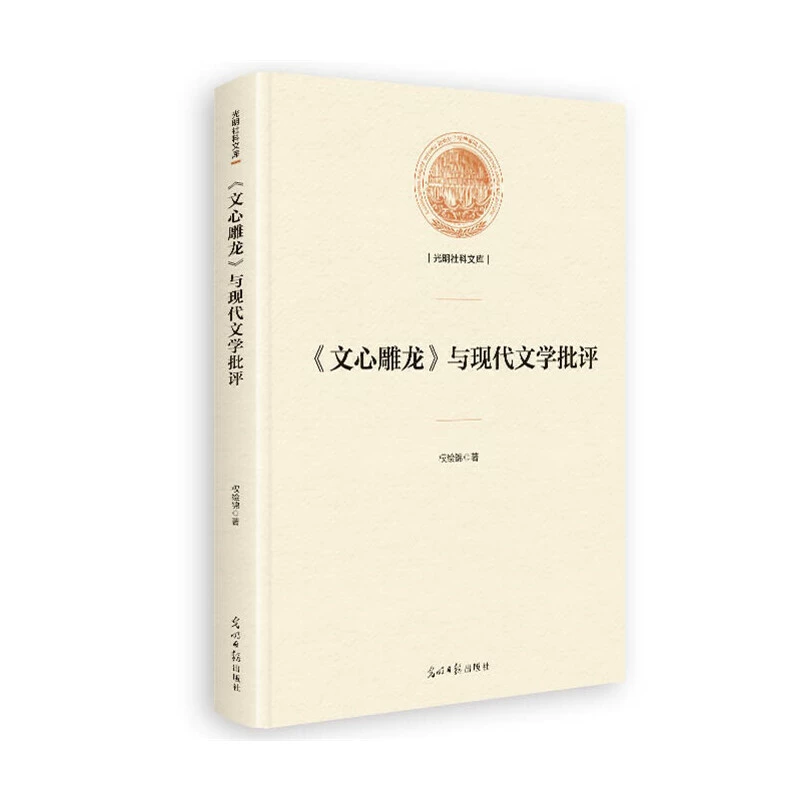
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戒之训。(《铭箴》)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杂文》)
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论说》)
虽复道极数殚,终然相袭,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辙焉。(《封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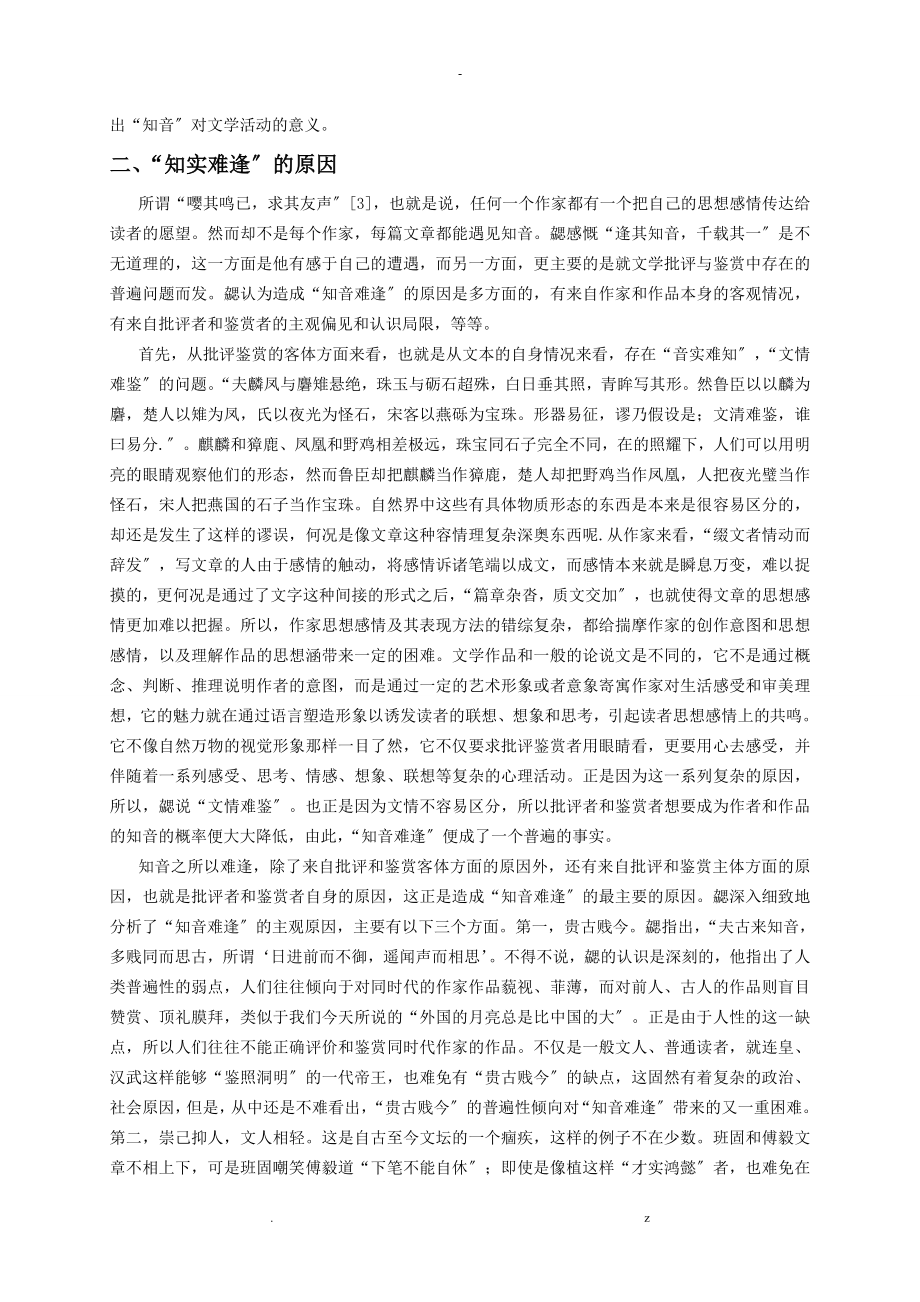
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奏启》)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
战代枝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养气》)
“日新”精神贯穿于《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各个方面,既包括文学本体的“原道”“宗经”,也包括文学体裁的“杂文”“论说”“封禅”“奏启”;还包括文学创作方法的“通变”“养气”,“求新求变”成为文学批评的理论追求。在《文心雕龙》的理论话语里,“日新”是一个核心语词,围绕“日新”的总体思想,《文心雕龙》还出现了“追新”“维新”“意新”“逐新”“知新”。文学理论话语里,“新”是文学的总体原则,《文心雕龙》崇尚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追新”“逐新”“维新”,这对我们构建新时代的文学话语体系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语境下,文学的“日新精神”应该具有中华民族的本位立场、沟通中外的世界眼光和融入现实的时代气象。
在社会激烈变化、时代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坚守中华文化的本位立场,赓续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更成为古代学术的历史传统。从中华民族的立场出发,“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一直是中国式学术坚守的基本理念。中国式文学批评的民族立场坚守,首先应该基于中国文学的基本事实,在传统文学的思想传统和艺术精神里,寻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时代语境。
现代化的本来意义就是相对于世界性而言的,脱离世界的整体环境不会存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单独的现代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也必须从世界性的角度来说才有意义,文学的通变也从古代的“古今之通”,演变为“古今之通”与“中外之通”的融合。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历史从“世界历史”向“世界的历史”的转变,即历史从局部的孤立的单独的历史事件,转向联系的沟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与此相适应,文学也从“世界文学”转向了“世界的文学”,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文学”的意义就是“世界的文学”。这也就要求文学批评的眼光也应该是“世界眼光”。文学批评的“世界眼光”,即钱钟书所谓“打通”,不仅贯通古今,更应该沟通中外。
文学理论的创新总是基于现实的,融入时代精神和时代气象的(两学一做)习近平总书记以突出的创新性,脱离时代的语境,所谓创新只能是不着边际的口号而已。“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创作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风貌,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有一个时代独特的思想主张和艺术话语。文学批评的中国式话语,必须面向中国文学的历史现实,解答中国文学的时代问题。在世界文学的历史环境中,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独特语汇,在文学理论上发出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