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雅哥说
本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强所作《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中《绪论》之一节。
在本篇文章中,刘勇强教授从古代小说在传统文化中地位出发,主要从其现实性、对伦理道德的重视、主客观相结合、情节性和体制等方面,探讨了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
Vol.480
通识经典
古代小说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民族特点
刘勇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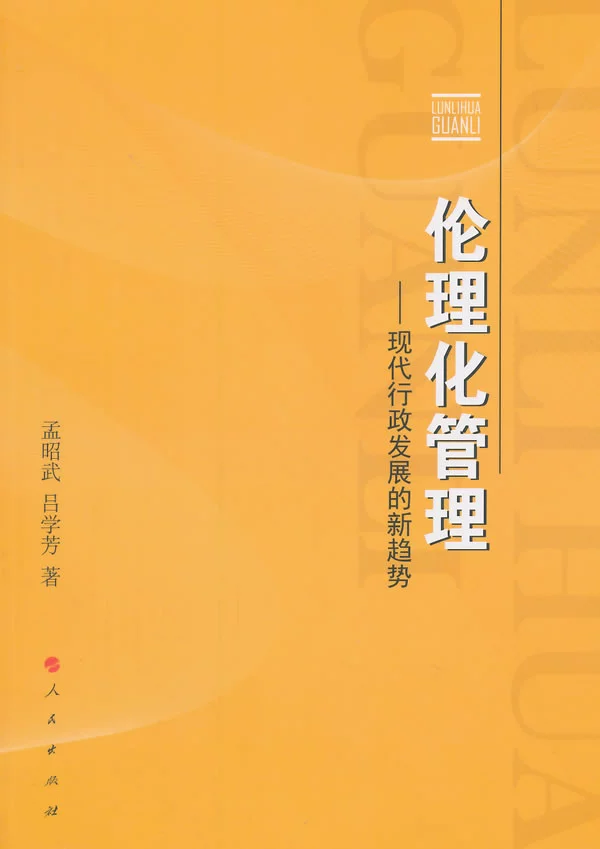
北京大学中文系
按照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分类,小说属于子部,在子部中还常列入“杂家”中,有些则被列入了史部,但是属于杂史、野史之类。这指的还是文言小说,若是通俗白话小说,则极少被正规的书目著录。这很典型地反映了小说这一文体在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它基本上被看作严肃的文学、文化活动之外的一种写作。因此,从接受的角度说,小说也往往被当成一种消遣。
有关小说创作与接受的贬低性言论在古代典籍中数不胜数,即使在明清时期,小说早已事实上成为大众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和社会文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载体,在正统的观念中,仍然是受歧视、被排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小说史,也是小说不断争取自己地位的历史。如上所述,这种努力体现在历代小说家坚持不懈地向历史和道德两个方向的靠拢。
不过,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毕竟是来自下层社会的文艺形式,除了不可避免地带有主流文化的烙印杂家小说,也必然深深地反映着非主流文化的特点,例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江湖义气,就来自民间,是这两部小说的精神命脉。《西游记》中的三教合一固然是唐以来社会思潮大趋势的影响,但也反映了民间的圆融混杂的观念。即使是上面提到的劝惩,也并不局限于正统的伦理道德,而往往与世俗社会的生活观念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古代小说始终摇摆于雅俗之间。就文体而言,它一直被视为俗文学,但每一部作品的文化特性却不那么简单,例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较其早期同类作品都有明显的雅化或儒化倾向,而这种雅化或儒化并不是单一的,俗化倾向也同时在发展。至于《红楼梦》更创造了雅俗交融的典范。
正是由于小说具有兼容雅俗文化的特点,它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小说创作走向高潮的明清时期,小说已成为精神文化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以致有人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1]
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就是由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决定的。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中国古代小说逐渐形成了一个体多性殊、具有广泛适应性和灵活性的艺术体系,其间也包含着小说思想内涵与艺术理念的一些具有历史性、普遍性的共同追求。

图为《红楼梦》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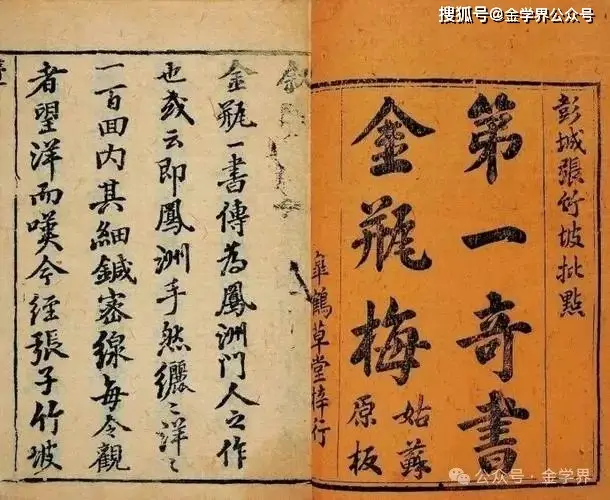
首先,无论是哪一种体式的中国古代小说博雅哥说:古代小说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民族特点,都能直面社会与人生的现实问题,具有很强针对性,即使是上古神话,也多具有很强的现世色彩;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虽以怪异为旨趣,以“辅教”为目的,却在鬼魂精怪的描写中,揭露了社会的不合理、政治的黑暗等,其尖锐性不在同时志人小说之下;唐代的传奇在现实性方面较志怪小说又有明显的发展;明清时期的《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更自觉地通过非现实的形象构成,反映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宋以后兴起的通俗小说,适应市民社会的需要,更直接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明中叶以后,小说家们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主张描写日用起居、人情世态,现实性进一步加强。这当中还有一些作品,与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战争频仍的时代特点相联系,表现了鲜明的反抗残暴、向往和平以及忠君爱国和或隐或显的民族情绪。无庸讳言,在古代小说中,也有许多回避与粉饰现实的作品,例如宋代传奇在文体上虽有所发展,但津津乐道的隋炀帝、武则天、唐明皇等故事,又缺乏深入的开掘,现实意义就相对贫弱。明清的神怪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也有不少出于杜撰,思想流于平庸。
中国传统文化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同样构成了古代小说思想观念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这一特点,如果仅仅理解为一种道德的说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实际上,古代小说中的伦理道德意识,内涵是很复杂的,对作品形象塑造与情节体系的作用也不一样。这里,至少可以从正义感、伦理感和道德感三个层面来理解。
所谓正义感,就是指古代小说中同情弱者、反抗邪恶、主持公道的思想感情。这本来也是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一个传统,司马迁作《史记》,就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对刘邦有微词,对项羽则较多同情,其间正包含着对王霸者的轻蔑、对失败者的惋惜。小说生于民间,天然具有扶弱抑强的意识。《搜神记》中的名篇“韩凭夫妇”,被宋康王逼迫双双殉情的韩凭夫妇,虽不能合葬,坟上却长出了根交于下、枝错于上的“相思树”,这是对凶狠、残忍的权势者的抗议,也是弱者的善良愿望。《古今小说》中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宋四公身为偷儿,因为目睹了张员外欺负一个乞丐,所以百般戏弄他,同样流露出市民社会的正义感。
所谓伦理感,主要是指对传统的伦理纲常、忠孝节义之类思想的宣扬,其中自有落后保守的一面,末流更训诫连篇,不堪卒读。就小说史而言,以宣传伦理纲常为自觉的目的,是在宋以后,也就是理学兴盛以后。但在涉及具体的历史政治与社会关系时,则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应注意作者的观念、作品中的议论与形象的客观意义的不同。在有些作品中,所谓伦理纲常是有特定含义的,如《三国演义》就将正统观念与“拥刘反曹”的政治态度结合在一起,使看似抽象的伦理纲常有了明确的、贴近大众的意义。
所谓道德感,主要是指对见义勇为、舍己为人、守信用、重然诺等一般的道德原则的肯定,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极力赞颂的,如《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等,都是下层人民道德理想的集中体现。道德感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如《醒世恒言》中《施润泽滩阙遇友》所赞美的那种拾金不昧的道德杂家小说,在追金逐利成为一时之尚的明中后期,就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在肯定与弘扬伦理道德的同时,古代小说相应地对道德败坏的现象与人物作了批判性描写,从而使所谓“敦教化、厚风俗”的儒家思想在小说的艺术世界得到形象的体现。

图为《三国演义》插图
在艺术理念上,中国古代小说首先重视真实性。从小说的描写看,则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说早期小说的真实性更多的是一种纯客观的真实的话,那么,后期小说的真实性还注意到作者的主观感受,所以曹雪芹一方面坦承了自己的包含着“一把辛酸泪”的真挚感情杂家小说,另一方面又强调“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的创作原则,主观感与客观真实的结合,成就了这部小说的艺术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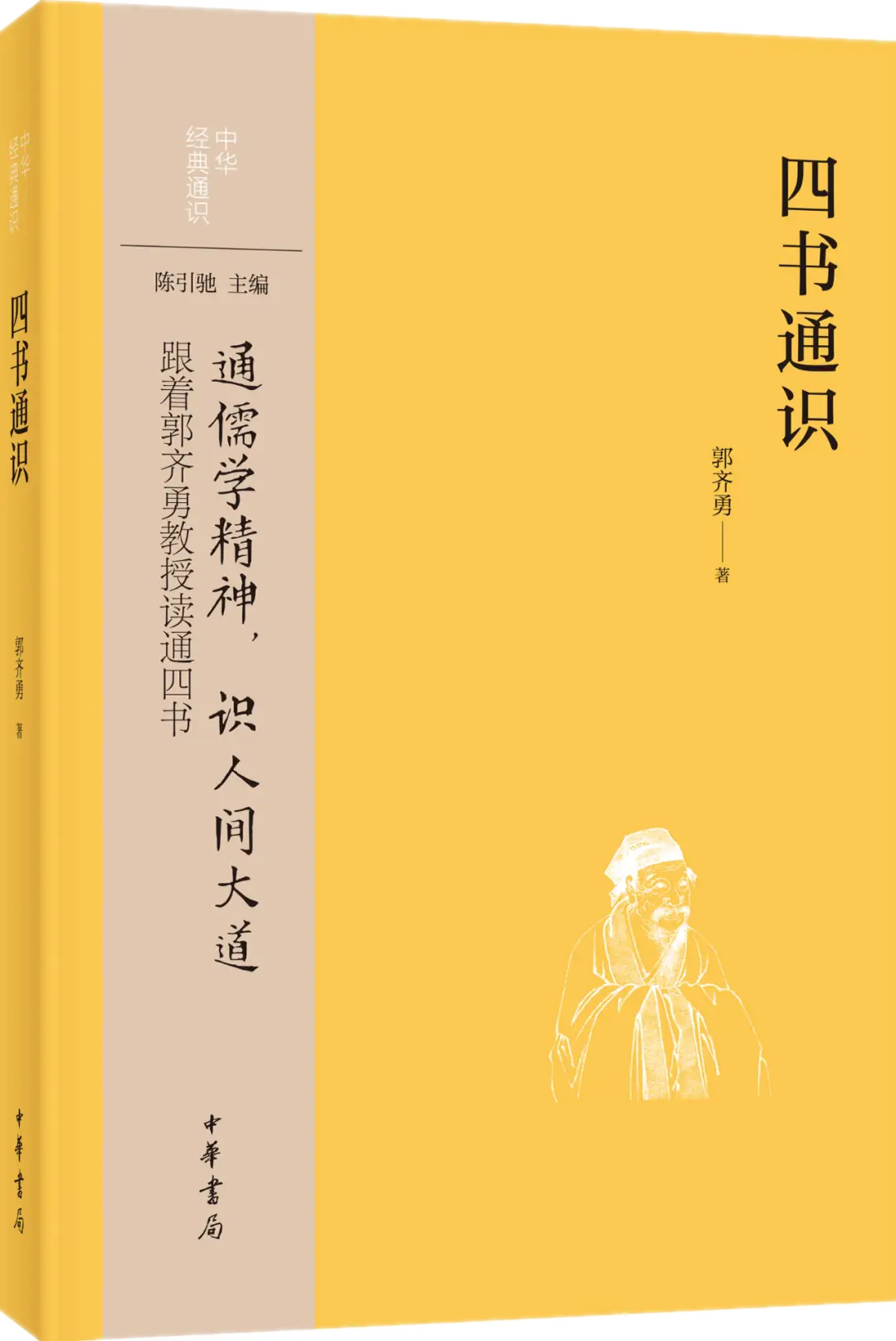
在真实性上,史传文学为对小说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史传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地反映时代面貌与历史人物,提倡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尽管史传的真实与小说的真实有所不同,但某些普遍的经验还是有启发意义与借鉴作用的,所以金圣叹说:“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例如在人物刻画上,史笔要求“不虚美,不隐恶”的客观态度,并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写出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心理,这对小说就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水浒传》写林冲、武松、李逵等,《西游记》写猪八戒,《红楼梦》写贾宝玉、林黛玉,都采取了“爱而知其丑”的态度,而《三国演义》写曹操,《红楼梦》写王熙凤,则是“憎而知其善”的。正因为小说家善恶必书,这些人物才更显得真实感人。
不但如此,中国古代小说还从其他艺术那里吸取成功的经验,例如它讲究“神似”和“境界”,这可以说是更高程度上的真实。“神似”是从绘画那里来的,“丹青难写是精神”,“神似”就是要写出人物的内在品格与精神底蕴来。如《西游记》中取经四众,形态各异,深刻地体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实际上,明清小说评点中,常以“神似”评品人物塑造,所谓“追魂摄影”、“骨相俱出”、“遗貌取神”等等,都表明“神似”已成为普遍的、自觉的审美追求。同时,中国古代小说借鉴诗歌的经验,提倡境界或意境,也就是不一般地向读者、听众叙述故事,而是把读者、听众吸引到一个特殊的艺术场景和氛围中,感受情节的内在意绪,比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去世的“秋风五丈原”一节,就以感人的笔墨烘托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气氛。《红楼梦》也有许多极富意境、韵味的描写。由于突出了“神似”、“境界”,真实性在这里就不只是纯客观的、浮面的东西,而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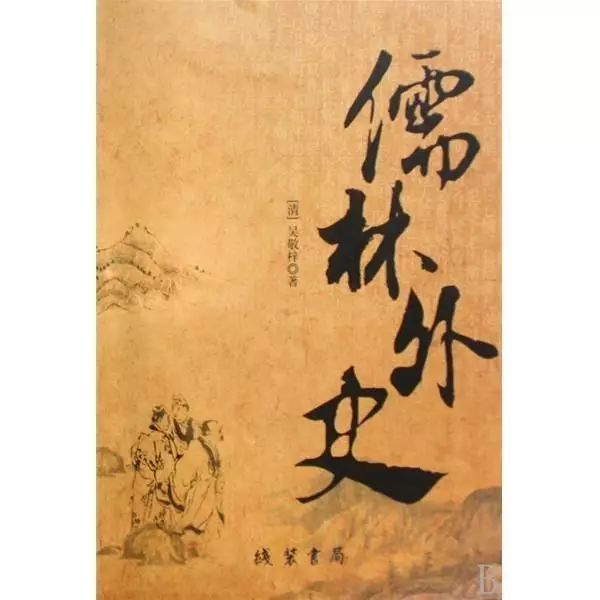
图为《儒林外史》
其次,中国古代小说还很重视情节性。作为小说的一个要素,情节性在古代小说中也是逐渐发展提高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中,或者仅粗陈梗概,如一些志怪;或者只有一些片断细节,如一些志人小说。唐代传奇的情节渐趋曲折、丰满。而宋元说话艺术,由于艺人们竞相招揽听众,更注意以惊心骇目的情节吸引人,“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长久”。[2]随着文人独立创作的普遍化,富于情节性的特点仍被继承下来博雅哥说:古代小说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民族特点,不过,一些高明的小说家已不刻意追求外在的“奇”和“巧”,而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编织故事,于平淡中见波澜,如《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写的都是一般的家庭琐事、世态人情,但又能在“庸常”中见“真奇”。[3]
古代小说的情节性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是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说来,它的情节具有单向性,无论采用什么写法――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横云断岭”等――都循序渐进,推因及果,一以贯之,脉络分明。与此相关的是,它的结构多严整统一,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起承转合,头尾完整,段落分明。其间固然不免有所谓“封闭性”的缺点,但一些优秀的小说家却能在这种封闭性的结构中求得开放的效果,如《金瓶梅》在西门庆死后,又点出一个张二官,使读者能从西门庆一家的故事中跳出来,看到它的普遍意义。从具体描写来看,古代小说不象一些西方小说那样常静止地描写客观景物和人物心理,而是赋予形象极强烈的动作性,不但使读者始终保持盎然的欣赏兴趣,而且使环境描写成为人物的一种活的陪衬,人物心理也呈现出更丰富、更微妙的特征。事实上,人物与情节的关系在小说中并不是二元的,古代小说以人物为情节的中心,人物的性格总是通过他们的行动表现出来的,如关羽的英雄形象就是在屯土山约三事、挂印封金、霸桥挑袍、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等一系列重大情节冲突中凸显出来的。通过情节写人物,还便于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古代小说对情节的重视,目的在于使读者在“通事”的基础上“悟义”、“兴感”[4],把握情节的内涵,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而由于突出了情节,即使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农夫小贩,也能把小说中生动的故事与人物讲评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换言之,古代小说因此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古代小说在叙述语言上,还讲究精炼简洁,不但文言短篇小说力求达到辞约而旨丰,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的长篇小说,虽洋洋洒洒数十万、上百万言,作者也往往惜墨如金,以求一字而传神,用最准确、最经济的词句,表现最深刻、最丰富的内容。这当然不只是语言问题,在对生活现象的概括提炼方面,更是如此。小说家总是努力抓住富于特征性的东西,表现社会的内在本质。既善于剪裁,缜密构思,又层层深入,精雕细刻,在芜杂的材料中,抉剔精髓,加以扼要利落的呈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详略得当,轻重相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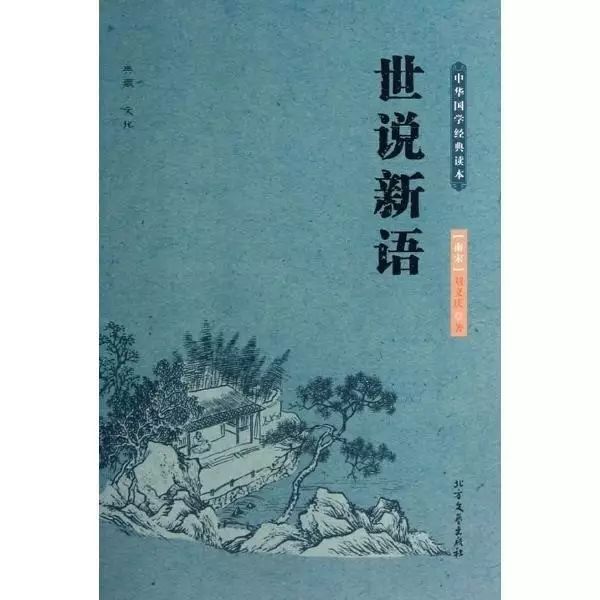
图为《世说新语》
古代小说艺术上的特点还与它的体制有关。众所周知,古代小说中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各成系统,同时又彼此关联,互相影响。思想、题材、叙事范型以及手法的借鉴自不待言,语言方面也多有交融。文言的凝炼精警与白话的生动活泼相互生发,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虽用白话写成,但由于作者文化修养深厚,叙述语言俗中有雅,淡而有味。《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则相反,用的是文言,却我绝不晦涩,前者“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创造了一种适合历史演义的浅近文言,后者则在高雅淳正中,充满了生活气息。
与此相关,文白相间、韵散结合,也构成了古代小说的一种文体特色。早在《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于瑶池之上,即以二人吟咏的诗歌插入叙述文字中,既传达了两人的心情,婉曲动人,又使行文活泼而有变化。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穿插诗歌的亦复不少。唐代是诗歌繁荣的时代,传奇又“文备众体”,用诗更多,其中多为主人公酬唱赠答、抒情叙志之作,也有一些纯系游戏笔墨。而在当时的讲唱文学中,韵文与散文则同具叙事功能,这是一个突破。宋元说话艺术中,说白与念诵各有分工,韵散功能遂有所区别,一般散文叙述故事,韵文则品评人物、描摹环境、渲染情节,起到点明思想内涵、调节节奏、烘托气氛的作用。到了后世的文人小说家手中,韵散分工基本上也沿袭说话艺术的传统,在叙事的散文中间,常常加入骈韵文,或议论评介,点明题旨;或写景状物、烘托气氛;或为人物的抒情叙志,或为作者的显扬才学。韵文与散文的配合符合古代读者的欣赏习惯,成功之作如《西游记》、《红楼梦》等,韵散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当然,小说中的韵文也有用得不好的,如词赋绘物状景、描绘人物肖象,颇多雷同;韵文穿插过多,也有破坏情节与人物行动连贯性之弊;更严重的是一些韵文说教意味过浓,往往扭曲了情节的客观意义。
就篇章结构而言,古代小说也千姿百态。在文言小说中,有的只撷取一个细节或生活片断,以简炼之笔写出人物性格的某一点,如《世说新语》;有的则表现人物一段完整的经历乃至一生。白话小说无论篇幅长短,大都比较完整,开阖自如,疏密得当。由于白话小说源于说话艺术,而说话通常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讲完,于是就有了段落的划分问题,逐渐产生了章回结构,一般说来,章回的划分在情节的转换阶段,有一定的悬念,而一个或若干个章回构成一个情节单元,既连接前后文,又相对独立,使情节发展的阶段性和节奏感表现得更鲜明强烈。明清时期,章回体日趋精制化,《红楼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古代小说在结构体制上的特点,还有一些是由于创作与接受上的不同造成的。以话本小说为例,说话人作为叙述者与文人的写作就有所不同,他必须始终牢记听众(“看官”),尽量使情节连贯、完整,头绪不纷繁,尽量不使用倒装手法,为了吸引吸众,他要添油加醋,铺陈敷演,要故布疑阵,巧使“关子”。而为了显示自己的客观态度,便于与听众交流,说话人还往往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等等。其中不少特点后来也为文人创作所继承,但因为“讲――听”与“写――看”毕竟不同,说话作为一种包含表演的艺术方式不可以一成不变地体现在书面化的读物中,有的只是因袭了一些“套语”而已,而文人为阅读所创作的小说,也自有其优势,不必受限于说话人所必须依循的种种限制。不过,即使是以文字为传播媒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也总是拟想自己在对听众讲故事,这种始终以接受者为中心的创作态度以及由此派生的叙事特点,是应予积极评价的。
[1] 钱大昕《正俗》,《潜研堂文集》卷十七。
[2] 罗烨《醉翁谈录》卷一《舌耕叙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
[3] 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见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792页。
[4] 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见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8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