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文本的根源有三个特点不可缺

《庄子》之中诸多涉及先秦人物的记载都是“寓言”,所以全系凭空捏造,全然无足信据,这种观点目前在学界仍然会时常遇到,甚至有学者以此为“常识”并用之教导后学。实际上这种观点是20世纪初产生并广泛流传的对《庄子》文本的一种误读,其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三,下面一一分述。
寓言一词翻译时产生的误差
寓言(fable)是一种特殊的西方文学体裁,一般以比喻或拟人的故事寄寓意蕴深长的道理,其以《伊索寓言》最为典型。作为文学体裁的寓言至少有三个特点不可或缺:一是虚构性。寓言的内容和情节都是作者独具匠心的虚拟,没有事实或历史根据;二是人物具有性格,故事具有情节;三是鲜明的教育性或讽刺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伊索寓言》传入中国之初其被翻译为《况义》,“况”即比况庄子.寓言,“义”即寓意。在清代《伊索寓言》又被翻译为《意拾蒙引》,其中使用“蒙”字无疑是因为翻译者看到了寓言对少年儿童的启蒙作用,而使用“引”字则很可能是因为寓言具有引人思考的意蕴。无论是“况义”还是“蒙引”,都说明前人已经注意到了寓言这种西方文学体裁的特殊性,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与之严格对应的词汇。1902年林纾等翻译《伊索寓言》时首次使用了“寓言”一词来翻译“fable”,而沈德鸿(茅盾)先生则在1917年编成《中国寓言(初编)》,孙毓修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寓言”一词与西文“fable”的对译关系。自此以“寓言”一词来翻译“fable”被正式认可,进而广泛流传开来。
但是,按照上文所列举的作为文学体裁的寓言所具有的三个特点来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fable”一词与《庄子》所说的“寓言”其实是不对等的:
第一,“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在《庄子·寓言》对“寓言”的描述性定义之中没有虚构假设的含义。因为人们都喜欢“与己同则应庄子.寓言,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所以《庄子》书中除了直接地发表观点和议论之外,类似于亲生父亲不方便亲口夸奖自己的儿子而引述外人赞誉儿子话语的情况,庄子引用了他人话语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求更好地说明意指。简单来说,就是引用他者话语申论己意《庄子》文本的根源有三个特点不可缺,其中绝对没有伪造他人话语的含义。
第二,《庄子》中很多人物性格模糊,大多数记载缺乏情节或情节不完整。比如《逍遥游》中蜩与学鸠对大鹏的“扶摇直上九万里”发表了议论,其中仅仅是出于一般鸟雀的立场来表达对大鹏鸟的不理解以及对自己所处境遇的满足,蜩与学鸠的性格并不突出。《庄子》中的很多内容都是人物对话,根本就没有什么情节,比如孔子与老子的多次会面。
第三,哲学著作《庄子》中频频出现的人物对话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并不通俗易懂,也没有“鲜明的教育性或讽刺性”。即使因为《庄子》中的某些片段可以视作寓言故事甚至用于儿童教育,但是因为其具有深刻内涵而与一般的浅显易懂的寓言故事判然有别。
总之,把《庄子》寓言直接理解为“用假托的故事或者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带有讽刺和劝诫的作用”绝对是不合适的,并不符合《庄子》文本。
对《史记》相关记载的误解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的记载非常简略:
庄子者,……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司马迁的这段话引发了司马承桢等学者的误解,其中的关键是:司马迁所说的“寓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司马迁所说的“寓言”是指伪造他人言论的话,那么接下来司马迁只是在举例论证他的判断,即列举了《庄子》中的部分篇章和内容并说明其别有用心之旨,揭示其捏造事实之处。所以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庄子》这本书全部是“假托之言”,其用意是“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所出现的人物“皆空语无事实”。
《庄子·寓言》有“寓言十九,藉外论之”,意即《庄子》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藉外论之”的寓言,所以司马迁应该是据此做出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
寓言也”这样的判断。如果说“寓言十九”是司马迁作出“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这一判断的直接根据的话,那么司马迁所说的“寓言”就是《庄子》中的“寓言”,二者同义,都是“藉外论之”,丝毫没有作伪的含义。
在做出《庄子》寓言居多这一判断之后,司马迁对《庄子》一书还做出了一些澄清和批驳,这是《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所导致的问题,需要细致地加以辨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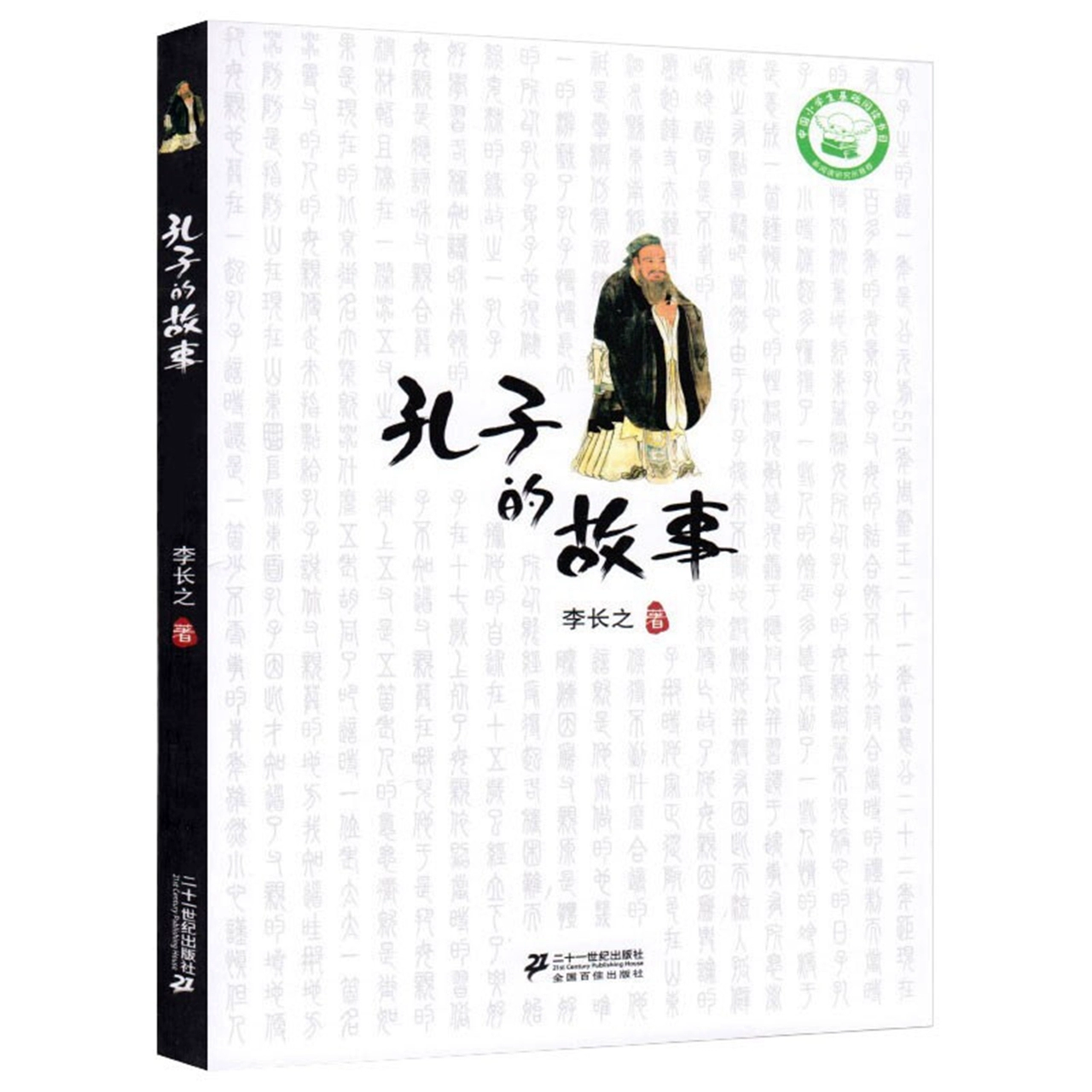
首先,因为《庄子》一书收录了很多当时著名人物的论道话语,其中必然收录了很多涉及孔子及其门徒的文献资料,这也说明了孔子及其门徒在当时思想界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至于其中哪些是对孔子言行的忠实记载,哪些是修辞夸张的虚托造作,这就需要对具体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其次,按照今天的《庄子》版本,《渔父》、《盗跖》属于杂篇,《胠箧》属于外篇,它们很可能不是庄子亲作,而是出自于庄子后学《庄子》文本的根源有三个特点不可缺,所以司马迁认定《渔父》、《盗跖》、《胠箧》三篇系庄子亲笔所作这不甚准确。
第三,虽然《盗跖》之中出现了盗跖对孔子大加批驳的明显渲染过度的情节,但是就总体而言,《庄子》一书中的孔子及其弟子大都是以正面或中性形象出现,对其言行的记载也比较笃实。司马迁的论断“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对于《渔父》、《盗跖》、《胠箧》三篇来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对于《庄子》全书而言这一判断则不能成立。孔子在《庄子》之中有很多正面甚至是光辉的形象,比如《秋水》就有孔子“畏于匡”(《论语·子罕》)时坦荡言行的珍贵记载。可见,在《庄子》中并没有尊老贬孔的明显而一贯的思想倾向。
最后,今本《庄子》中根本就没有《畏累虚》、《亢桑子》这两个篇名,更没有直接出现“畏累虚”和“亢桑子”这两个名字。现在看来,司马迁很可能是根据当时流行的其他《庄子》版本认为“畏累虚”和“亢桑子”为代表的虚拟人物“皆空语无事实”,而不是指认《庄子》全部内容都是胡编乱造。
因此,司马迁是在《庄子》“藉外论之”的语义之下使用“寓言”一词,他只是针对《庄子》一小部分内容加以指摘和澄清,并没有全盘否定《庄子》内容的真实性。
文学研究视角的局限
《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先生“庄子名周,宋之蒙人,盖稍后于孟子,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之语实是对上文所引《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于庄子记载的摘要和提炼;司马迁对于《渔父》、《盗跖》、《胠箧》三篇的批评,对“畏累虚”、“亢桑子”的分辨,全部被省略。从中不难发现鲁迅先生对《庄子》寓言的误解:“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由于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崇高地位,由于其《庄子》文学研究的示范作用,其对于《庄子》寓言“皆空言无事实”的定性可谓影响深远。鲁迅先生把《庄子》寓言全部当做“空言无事实”的文学作品来处理,实际上也就是把《庄子》寓言的研究角度限定为文学研究,进而全盘否定了其历史文献价值。《汉文学史纲要》系鲁迅先生1926年在厦门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那时候“寓言”已经被当做翻译“fable”一词的中文定名。所以鲁迅先生当时应该是已经知晓并接受了以“寓言”来翻译“fable”,进而在其《汉文学史纲要》的创作中受到了西方文学体裁概念下寓言一词“虚构”含义的影响。从另一方面来看,受到司马承桢等学者的影响,鲁迅先生也对《史记》中关于《庄子》寓言的话语产生了误解。
闻一多先生关于《庄子》寓言的看法比鲁迅更加激进:“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起的”,“《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都是庄子的赐予”,“谐趣和想象打成一片,设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结果便愈能发人深省——这才是庄子的寓言。”把《庄子》寓言视做纯粹的文艺作品,枉顾其本初含义,这种看法已经被现代学者注意到并加以批评:“闻先生过于偏爱《庄子》中的文学成分,故将《庄子》所谓‘寓言’与《庄子》中的寓言故事混同。既误解了‘寓言’称谓的含义,又夸大了寓言故事的文学意义。”
鲁迅和闻一多两位先生对《庄子》寓言全系文学作品而完全没有先秦史料价值的界定一直被继承下来庄子.寓言,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再三确认。
《庄子》寓言就相当于在现代文体中经常出现的引用他人话语,而引用他人话语当然不意味着引用者捏造他人话语。即使《庄子》因为各种其他原因而羼入今天看起来“很可疑”的部分内容,这也应该是先秦古籍在流传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庄子》寓言的含义不理清,先秦道家研究就难以深入,庄子及其门人弟子更会始终被指认为“说谎者”,古人可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