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为有名”的性-伪说
——论《礼论》《正名》《性恶》的性-伪说
文章中()是上图“伪”字
二、《正名》对性、伪的界定及对心、欲的讨论
与《礼论》主旨不同,《正名》主要讨论“名”也就是概念的问题,故对性、伪等概念做了严格定义,代表了荀子对人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荀子认为“所为有名”也就是正名的目的是“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这里的“实”包括了“贵贱”和“同异”,前者可归于伦理的范畴,后者属于认识的领域。“明贵贱”之名乃名分之名,指人伦之间各种关系之名,即《正名》所说的“刑名”、“爵名”、“文名”等典章制度之名。“别同异”之名乃名言之名,指具体事物之名,也就是荀子所说的“散名”。故荀子的正名既包括正名言之名,也包括正名分之名,前者乃名学或逻辑意义上的正名,属于实然的领域,是对名家“析辞擅作名”的批判和回应,目的是区别事物或认识对象之同异,进而分辨认识上之是非;后者是伦理政治意义上的正名,属于应然的领域,是对孔子“正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目的在于规定人伦关系中的名分、职责。故荀子之正名实具有名学或逻辑和政治伦理的双重内涵,二者分属不同的领域,但荀子并不做严格区分,而是试图将二者统一在一起,而统一的关键乃在于关于人之散名。故《正名》开篇称:“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注:旧俗乡约),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刑名、爵名、文名以及万物之散名均有相应的定名原则,其主要讨论的是“散名之在人者”: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性伤谓之病。节遇谓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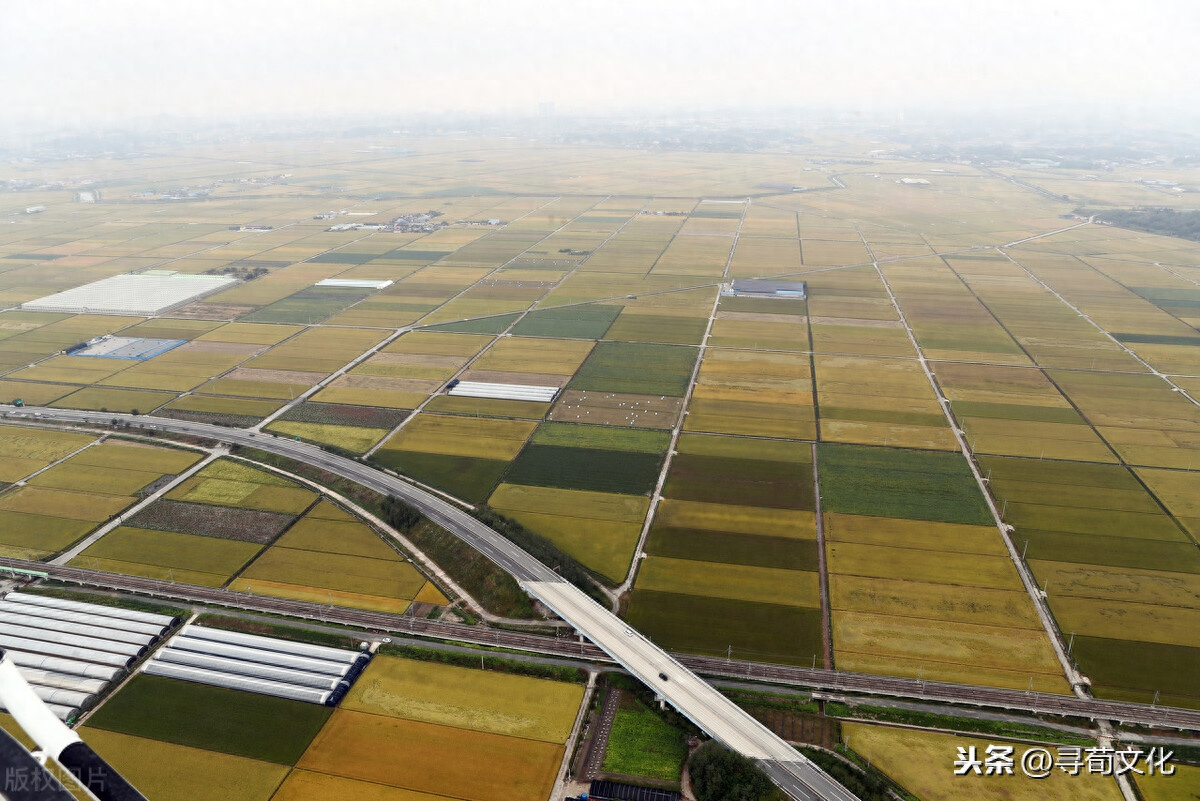
这里荀子对性、伪、知、能均做了两层定义,使其具有一种双重结构,反映了荀子对人性问题的理解,虽然上文称“是后王之成名也”,但实际是荀子的独创。这里的“后王”乃后起之王,也就是荀子心目中的理想之王。其中关于性的第一层定义是说,人生而如此的内在原因、根据即是性,“所以然”是就生之现象更进一步求内在根据,在荀子这里就是指生而所具的禀赋、资具。故第一义的性实际有两个条件,一是人生而所具有的,二是规定了人的基本特征的。按照这一定义,“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的欲无疑是属于性,而知甚至爱也可以归于性,这在荀子那里也是有根据的,如“凡以知,人之性也”(《解蔽》),即明确肯定知就是性。又如,“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前面已说,这里将知、爱并举,故爱与知一样也是生而具有的,而且规定了人的基本特征,故理论上也可归于第一义的性。这说明荀子的“生之所以然之谓性”较之告子的“生之谓性”是一个发展,告子的“生之谓性”只是个形式的命题,只是就生而所具的食色来理解性,这样就无法突出人之为人的特征,势必将混同人性于犬之性、牛之性,故孟子对其进行批驳,用归谬法的形式指出“生之谓性”的局限以及告子以食色言性可能导致的谬误。
[ 参见拙文:《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哲学研究》,又见拙作:《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0~336页。]荀子对此可能已有所了解,故其谈性不再限于生理欲望,而是将情(欲)与知都归于性,形成所谓的二重结构,这在其前期作品《富国》《荣辱》中已有体现,故当《正名》对性进行定义时,提出“生之所以然之谓性”的命题,理论上将欲望与知能都概括其中,使其第一义的性有可能同时包括情性和知性,以与《富国》《荣辱》等篇的观点保持一致。不过荀子在以前的讨论中已经注意到,情性与知性在表现方式上并不相同,欲是生理本能,不用学、不用教,“是无待而然者也”(《荣辱》),而知虽然也是一种先天的禀赋,但其实际运用则要经过后天的认知过程,能知要落实在所知上。故对于知性而言,就不能只谈能知,只强调“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同上),更重要的是谈所知“所为有名”的性-伪说,要解释、说明“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富国》),而后者显然不能仅仅从性加以说明了,故荀子又提出性的第二层定义,将所知也就是知的运用排除出性。荀子关于性的第二层定义中,“性之和所生”是说性在和谐状态下产生的,“和”是对“性”的限制、修订;“精合感应”是指精神与外物相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是说不经人为努力,自然产生出来的就是性。
按照这一规定,所知或知的运用显然已不属于性了,因为它要经过有所事、有所为,是人为的结果,而非“不事而自然”。这样荀子在性的第一层定义中,将情(欲)、知甚至爱都包括在性之中,而在性的第二层定义中又将知和爱排除在性之外。由于荀子关于性的两层定义是一个有机整体,故在荀子那里严格说来,只有情(欲)才是属于性。但荀子关于性的定义又包含两个层次,其中第一义的性是性的本质属性,凡是生而具有的,规定了人的特征的都可属于性;第二义的性是前者的作用和表现,由于荀子规定了“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故只有生理欲望、自然本能才属于性。性的第一层定义避免了告子“生之谓性”对人性理解的简单化,以及可能混同人性、兽性的弊端,反映了荀子对人性问题认识的深化;性的第二层定义则将性主要限定在生理欲望、自然情感上,体现了荀子人性论的特色。故上文在性的两层定义后接着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好、恶、喜、怒、哀、乐乃性之表现,属于自然情感。竹简《性自命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喜、怒、哀、悲之气是性,其表现于外就是情,故又说“情生于性”荀子人性论的主要观点,其特点是“物取之也”,也就是外物的刺激感应。
喜、怒、哀、乐是一种狭义的情,广义的情也可包括欲。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正名》),“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节·礼运》)爱、恶即好、恶,欲与好、恶、喜、怒、哀、乐一样,也属于情。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欲往往是由生理机能和内在需要决定的,是“己取之也”,而不一定需要外物的刺激感应。“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情随感而应,“不事而自然”,而心则要对情的表现做出抉择、判断,这就是心之思虑。这里《正名》提出了心,较之以往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富国》《荣辱》虽然出现心字,但还不是严格的哲学概念,其心主要是经验心,虽个别情况下有意志的含义,但主要还指情感欲望。《正名》则不同,其心显然已是重要的哲学概念,故文中常常心、性(欲)对举,反复陈述,对心的重视程度决不在性之下,以往有学者称荀子人性论是以心治性,这一思想显然在《正名》中已开始出现了。《正名》没有将心列入“散名之在人者”,故没有对其做出明确定义,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在荀子那里,心是介于性和伪之间的概念,就心是天官或天君而言,它可归于性,就心的作用而言,它又属于伪了。故在《正名》中主要讨论了性和伪,而没有谈论心。荀子后来对心也做过定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解蔽》)但只是一层定义,而非二层定义。若就心的作用、表现做第二层定义,按照荀子的规定,就应该称为伪。故在荀子那里,心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就“心生而有知”(同上)言,可以归于“生之所以然”的性;就心的活动、表现言,则属于伪。心既属于性又不属于性,既属于性又属于伪。[ 参见何淑静:《孟子道德理论实践之研究》第三章《论荀子是否以‘心’为‘性’》,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第47~74页。]故荀子的心实际是一动态的概念,包括生而具有的认知能力(潜能),这种能力的实际运用,也就是心的思虑、认知活动,以及心在实际运用中进一步获得的知识、智慧和能力。
对于心既可以综合地看,也可以分解地看。综合地看,心只是一心;分解地看,心至少包括先天的知能,知能的运用,以及后天获得的能力三个层面,而后两个层面荀子均称其为伪。上文“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是第一义的伪,指心的思虑及其活动;“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是第二义的伪,指心在思虑活动的基础上获得的智慧和能力。葛瑞汉曾推测说,《正名》篇中“主要定义分为七对(引者注:指性与性、情与虑、伪与伪、事与行、知与智、能与能、病与命),其中三对(引者注:应为四对)以不同的意思定义同一个词。他(引者注:荀子)很有可能使用了偏旁部首用以标志不同字词,而这些为后世的书写标准化所泯灭。因为如我们所见,文中曾有一对用了不同的书写形式(‘知’不同于加上‘曰’字的‘智’,像《墨经》一样,它也因为书写的标准化而被部分删除”。[ (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页。]从“知”、“智”的例子看,葛氏的说法颇有道理,故第一义的伪原来可能是写作郭店竹简的“”字,指心之思虑活动,第二义的伪才是本字,表示人为、“伪造”之意。“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指生而所具的认识能力,即“心生而有知”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指认识、符合了外物对象后获得的知识、智慧,实际是前一种知的运用。
“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一句中的“知”,学者往往认为是衍文,应删去,非是。盖“知所以能”是指知之能,而非一般的能,如生理本能,“弗学而能”(《礼记·礼运》)之能,故荀子往往知、能并举,如“材性知能”,“知”需要落实到“能”,而“能”是指“知”之能。另,“知所以能”之“知”,或作“智”(宋浙本),或作“知”(巾箱本),[ 参见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2页。]从文意看,第一义的能是指先天才能,故“知”可能比较符合荀子的本义。“能有所合谓之能”,指先天才能在实际运用中培养的后天能力。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荀子在《正名》中实际对性、伪、知、能四个概念分别做了两层定义,之所以突出这四个概念显然是有原因的。其中,性与伪相对,代表了人生的两种不同的倾向,而知、能又与伪密切相关,荀子的伪实际是综合了知、能而形成的概念。这样荀子的人性论便形成了性、伪之分的特殊结构:首先,第一义的性理论上实际包括了情与知,而知又属于心,是心具有的能力,它们都属于“生之所以然者”。其次,情与知的表现有所不同,情是随感而发,“不事而自然”,而知则需要有所事,有所为,需要经过人为的努力过程。由于荀子将第二义的性限定为“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故只有情属于性,而“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心之知、能活动则只能属于伪了。这样第一义性中的情和心(指心之知、能),由于表现方式不同,又产生出第二义的性和第一义的伪,第一义的伪在实践过程中“虑积焉,能习焉”,智慧不断积累,能力不断提升,又形成第二义的伪,形成多层次的性、伪之分结构。另外,《正名》对伪的两层定义与《礼论》篇“伪者,文理隆盛也”显然有所不同,不可混为一谈。《礼论》的伪是指“文理”也就是礼之仪式、节文,而《正名》的伪虽然有两层定义,但均与主体的知与能有关,指主体的认知、实践能力,故《礼论》的伪既是《正名》的伪认知、学习的对象荀子人性论的主要观点,也是其创造、制作的结果。“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之伪“所为有名”的性-伪说,也就是第二义的伪,实际是以外在的礼仪之伪为思虑、实践对象,进而完成智慧、能力的培养的,而作为外在礼仪的伪归根结底也是由主体的伪尤其是第二义的伪制作出来的,《性恶》将其概括为:“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伪起”即产生第二义的伪,由第二义的伪进一步制作出礼义。而礼义在《礼论》中也称作伪,不过主要指文理也就是礼之节文、仪式。这样结合《礼论》与《正名》,《荀子》的伪实际有三层定义,而三种伪之间又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第一义的伪是心的运用、表现,而心一旦开始活动,便与第三义的伪也就是外在礼仪发生联系,而在认识、实践外在礼仪的过程中“虑积焉,能习焉”形成第二义的伪,并进而“伪起而生礼义”,进一步制作、完善第三义的伪。不过由于《正名》只采取二层定义,故伪的定义并没有将《礼论》的伪包括进来,而且如果将伪分作三层,难免有叠床架屋之嫌,在表述上也会陷入混乱,故在以后的《性恶》中,荀子不再用伪,而是用“积伪”、“伪故”来表示第三义的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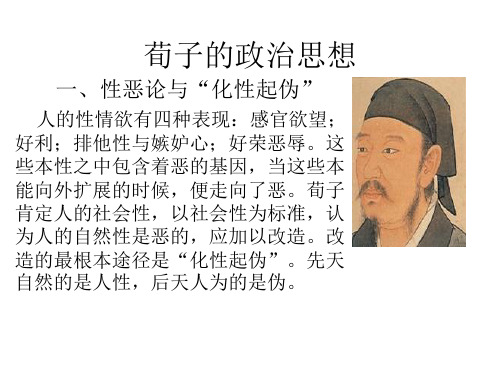
《正名》上半部分讨论名的问题,除了对“散名之在人者”作了规定外,还讨论了制名的三个原则,即制名之三标等问题,但下半部分则文笔一转,围绕欲与心的关系展开论述,似与正名的主题没有了直接关系。以往学者往往搞不清二者的关系,甚至怀疑《正名》是由两段不同的文字拼凑而成。[ 如日本学者物双松(荻生徂徕)认为,“‘凡语治’至篇末,当别作一篇,乃其辟宋钘者。”严灵峰编:《无求备斋诸子书目·荀子集成》,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41册第243页。]其实,只要了解《正名》的名主要是指名分之名,则以上的疑问便不难解答了。《正名》认为“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这里的名虽然包括名言之名,但主要是指名分之名。名分之名也就是孔子“必也正名乎”的名,是一种规范性的名,实际是与社会中每个人身份、角色相应的责任、义务。正因为如此,孔子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从这一点讲,名与礼实际密切相关,是礼的原则、依据。因此,正如《富国》《荣辱》从情性、知性的关系推出礼法论一样,《正名》也将欲与心的问题与正名论联系在一起。在《正名》看来,社会治理的关键是王者制定出正确、适宜的名,以此来统率民众,使其统一于名。但是“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名实的混淆导致政治的混乱,面对这一局面,一方面要探寻制名之道,“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并期待王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则要靠君子以心制欲,拒绝“邪说辟言”的诱惑,而接受符合于“治”的“正名”。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正名》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人只要合理地控制欲望,就能接受正名。但两者间显然存在着因果关系,不然就不会有《正名》后半部分的出现了。“在荀子看来,如果人心不会轻易受耳目左右,那么‘淫言’、‘奇辞’就没有那么容易眩惑人心了。‘名辨’思想家之所以会走向诡辩,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心’的正确引导,使‘耳目’陶醉、放纵于对国家有害的言辞游戏上。”[ 曹峰:《〈荀子·正名〉篇新论》,《学灯》2007年第4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正名》上半部分讨论了制名的问题后,又在下半部分对心、欲也就是情性与知性的关系展开讨论,故对于荀子人性论而言,《正名》的下半部分更值得重视。

从《正名》下的内容来看,荀子延续了《富国》《荣辱》情性、知性的二重结构,并从二者的关系探讨社会的治乱,只不过是从欲与心的角度展开论述的。在《正名》看来,治理的关键是处理欲望的问题,这实际蕴含着欲望可能会导致冲突,造成动乱的观点。但与《富国》《荣辱》一样,《正名》并不认为欲望本身是恶,也没有提出性恶的观点,相反认为,“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治理民众不能靠“去欲”和“寡欲”,而是要“道(注:导)欲”和“节欲”,而人之所以能够“道欲”、“节欲”是由于心的作用。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固难类所受乎天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注:通纵,舍弃)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
“欲”是先天本能,生理反应,不考虑可不可以得到;“求者从所可”的“求”是心的意志或欲求,要服从心之抉择、判断,需要心的认可。下面三句中,“一欲”,指相同的欲。《玉篇·一部》:“一,同也。”“心之多”,据杨倞注,当为“心之计”,指心之计度、思虑。[ (清)王先谦:《荀子集释》,《诸子集成》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影印版,第284页。]故人们所受于天的欲望是大致相同的,但受制于心的思虑、抉择,其表现已不同于所受于天的本然状态了。例如,人最大的欲望是好生恶死,这是“所受于天”者,但往往有人做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举来,这是心选择、决定的结果,是“所受于心”者。故决定我们行为的,不仅在于欲,更重要的还在于心,欲望过与不及,心往往能做出调整。因此,欲与心(知)的性质和作用是有所不同的。“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正名》下对性的定义与上略有不同,主要是没有对性做两层定义,而只是规定其为“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的情是指人情,即“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荣辱》),“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王霸》),也就是生理欲望。欲指生理欲望的反应、表现,即“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的欲。从“情者,性之质也”一句来看,《正名》上虽然对性做了两层定义,使其第一义的性理论上可以包括心或知等内容,但荀子主要还是从情来理解性的。《正名》上是分解地看待性,故有两层之分,而《正名》下则是综合地看待性,只强调性就是情(欲)。情或欲是盲目的,被动地受制于外在对象,没有是非观念,而知或心则是主动的,往往根据“可”也就是正确与否对情欲做出节制和引导。从这一点看,治乱在于心的抉择和判断,而不在于情欲的多寡和表现,而心抉择、判断的依据则是道或者理。“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心首先要认识道,不可以离开道或理而发挥作用,这是荀子的心不同于孟子心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正名》虽然提出了人性论的重要概念伪,但不论是在上半部分讨论正名,还是下半部分论及知与欲望的关系时,都是使用了心而不是伪。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伪()本来就是与心密切相关的概念,指心之作为,心之思虑活动。荀子提出伪之后,并没有取代心,而是二者同时并用。伪主要用来说明人性善恶的问题,解释化性起伪的道德实践活动,而谈到一般的认识活动,仍主要使用心字。《正名》上论及辩说时就是从心、道的关系立论的。“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象道,效法道。《广雅·释诂三》:“象,效也。”人们进行辩说,目的是要了解、认识道。工宰,学者一般从陈奂曰:“官宰者,官,工也。官宰,犹言主宰。”[ (清)王先谦:《荀子集释》,《诸子集成》第2册,第423页。]非是。《国语·晋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官宰食加。”韦昭注:“官宰,家臣也。”[ (三国吴)韦昭:《国语注》,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131页。]工宰,即官宰,也就是官吏。心是道之官吏,需要服从于心,故下文说“心合于道”。心合于道实际已涉及心之作为,故也可算作伪,但这里主要是讨论辩说等认知活动,所以荀子使用心字而不用伪。《正名》下讨论理、欲关系时也是使用心。“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社会的治乱不在欲望的多寡,而在于“心之所可”是否符合理。心之所可实际也包含了心之活动,心之作为,但主要是认识活动,故荀子依然用心不用伪。

前面说过,《正名》尚没有性恶的观念,但在对“性”概念的理解上已出现微妙的变化。《正名》上提出关于性的两层定义,其中第一层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显然是规范性概念,是从生理现象推进一层,是求“生之所以然”的根据,故实际是理,但不是道德义理,而是自然之理,是指事物的内在根据和规定。第二层定义“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特意点出“性之和”,强调是在性的和谐状态下感应而生,这种意义上的性显然也不是恶的。“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这里的情主要是情感之情,可能会有过与不及,伤害到性,“性伤谓之病”,而性本身不是恶。《正名》下则提出“情者,性之质也”,视情为性的本质,故是以情言性。此情是情欲之情,而非情感之情,故又说“欲者,情之应也”。既然“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那么,顺欲而为,不加节制,必然会导致争夺、混乱,结果是“嚮(注:享)万物之美而盛忧,兼(注:尽)万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养生也?粥(注:育)寿也?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享有万物之美,占有万物之利,所得的却是大忧、大害,这是 “以己为物役”,而非“重己役物”。这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是性(生)字,“养生”,即养性也。《正名》认为一味追求物欲而带来祸患并非是养性,这里的“生(性)”显然是规范性概念荀子人性论的主要观点,指合理的欲求,包括健康、长寿等,与《正名》上对性的定义一致,延续的仍是《富国》“害生纵欲”的观念。而“养其性而危其形”的“性”,则似乎更多是描述性概念,指情和欲而言,故“养其性”会“危其形”。这说明上面一段文字虽两次涉及到性,但内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由规范性概念转向描述性概念,故荀子分别用“生”和“性”来表示。而性一旦等同于欲,或者是从欲来理解性,实际便向性恶论打开了大门,或至少是向性恶论迈出一大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荀子对思孟“五行”说的批判-梁涛
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兼论统合孟荀三-梁涛
梁涛: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论礼论正名性恶的性-伪说一
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论修身解蔽不苟的治心养心说之一-梁涛